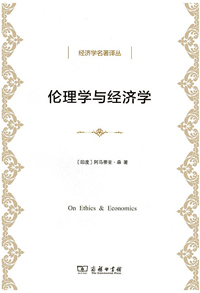 |
作者:(印度)阿馬蒂亞·森
出版:商務印書館
|
經(jīng)濟學研究注重數(shù)據(jù),、事實,、模型,,強調(diào)理性,、客觀,、中立,,但有些經(jīng)濟學思想也不乏宗教言說引人向善的旨趣,,有價值追求的經(jīng)濟學家會在求真的前提下把他的價值觀注入他的學說中,,比如1998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印度經(jīng)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代表作《倫理學與經(jīng)濟學》,。
阿馬蒂亞·森的書常常是大部頭,但這本根據(jù)他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洛爾講座講稿寫成的《倫理學與經(jīng)濟學》頁碼卻不厚,,但知識含金量,、思想密度一如既往地很大。森對當代經(jīng)濟學理論突出貢獻表現(xiàn)在社會選擇理論,、個人自由與帕累托最優(yōu)的關系,、福利與貧困指數(shù)衡量、饑荒問題與權利分配不均的關系以及道德哲學問題五個領域內(nèi),,《倫理學與經(jīng)濟學》是他用倫理學說明人類的經(jīng)濟行為,,用經(jīng)濟學闡釋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的著述。他認為,,經(jīng)濟學有兩個與政治學有聯(lián)系而聯(lián)系方式卻大不相同的根源:倫理學與工程學,。經(jīng)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詩人完全可以表達百分之百純粹且絕對與他人他物無涉的個人觀點,、情緒,但經(jīng)濟學家研究問題卻不能與世隔絕、向壁虛構,。所以為了說明經(jīng)濟學的傳統(tǒng)根源,,森把眼光轉回到2300年前,從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說起,。
亞里斯多德把經(jīng)濟學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lián)系起來,,指明了經(jīng)濟學對財富的關注。亞里斯多德把政治學視為“指揮者的藝術”,,強調(diào)政治學必須使用包括經(jīng)濟學在內(nèi)的“其他科學”,。雖然從表面上看經(jīng)濟學研究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直接相關,但在更深層次上,,經(jīng)濟學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關,,包括對更為基本目標的評價與增進�,!皰赍X是不得已而為之,,財富顯然不是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東西,只是因為它有用或者因為別的什么理由,�,!保ā赌岣黢R看倫理學》)亞里斯多德在論述國家在經(jīng)濟活動中的作用時堅決主張:“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正是因為這兩點,,阿馬蒂亞·森認定:經(jīng)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
在阿馬蒂亞·森眼中,經(jīng)濟學的所謂“理性行為”假設有很大缺陷,。以“理性行為”這一概念作為“媒介”來解釋實際行為預測問題是否有意義仍有爭議,,因為這里存在一個相當根本性的問題:即使標準規(guī)范經(jīng)濟學關于理性行為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邏輯自洽的,,且也被世人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就可以肯定,人們一定會按這種規(guī)范所描述的理性行為行事,。在真實世界,,人們會遇到種種顯而易見的困難,人都會犯錯誤,,常常要做實驗,,有時會感到困惑。所以,,這個世界其實是由哈姆雷特,、麥克白、李爾王和奧賽羅等常被“動物精神”力量支配的人組成的,。冷靜的理性范例充滿了我們的教科書,,但現(xiàn)實世界卻更為多彩,。
“理性行為”最重要的內(nèi)涵是所謂“自利最大化”,也稱為“自利理性觀”,,對此,,森剖析說,自利理性觀(self-interest view
rationality)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把任何偏離自利最大化的行為都看成是非理性行為,,就意味著拒絕倫理考慮在實際決策中的作用(不是某種被稱為“倫理利己主義”的外來道德觀或別的什么道德觀)。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xiàn)實的可能是一種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試圖用理性要求來維護倫理中的標準行為假設(即實際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領著一隊騎兵去攻擊一只跛足的驢,。
可貴的是,阿馬蒂亞·森并沒有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他并沒有全盤推翻自利行為假設:否認人們總是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并不意味著人們總是不自私地做事,,說自私行為在大量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私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作用,,正常的經(jīng)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自利和某種周全考慮之間并不存在著必然的矛盾,。只要系統(tǒng),、無偏見地閱讀和理解亞當·斯密的著作,自利行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是無法從那里找到依據(jù)的,。事實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qū)經(jīng)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癥式的生活,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jīng)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所以,森認定經(jīng)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jīng)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造成的,。
更可貴的是,,深切關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難的人們,被稱為“經(jīng)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的森并不只是泛泛而談“自利行為”,,而是深入該無形事物的深層結構之中,,條分縷析,,層層剝筍。據(jù)他的分析,,“自利行為”這一復雜結構有三個性質(zhì)完全不同——基本相互獨立——的特征:第一,,以自我為中心的福利(self-centred
werlfare):一個人的福利僅僅依賴于他自己的消費(尤其不存在對他人的同情和憎惡)。第二,,自我福利目標(self-welfare
goals):一個人的目標就是最大化他自身的福利,,以及(當存在不確定時)這種福利的概率加權期望值(尤其不直接重視他人的福利)。第三,,自我目標選擇(self-goal
choice):每個人的每一種行為選擇直接受其目標引導(其他人所追求的目標被給定,,不會因為認識到各自成功的相互依賴性而被約束或調(diào)整)。這當然是流行的主流經(jīng)濟學對“自利行為”的概括,,但是,,現(xiàn)代福利經(jīng)濟學并不茍同這種觀點。現(xiàn)代福利經(jīng)濟學固然關注個人,,但更關注個人福利與他人,、社會的相互依賴性,現(xiàn)代福利經(jīng)濟學把一個人的福利建立在比個人消費更加廣闊的基礎之上,。暗含在人類行為中的與上述三個特征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各種倫理思考,,實際上是能被系統(tǒng)地測試出來的。在博弈論所宣揚的人所皆知的“囚徒困境”中,,每個人都想有一個“嚴格占優(yōu)”(strictly
dominant)的個人策略,,其大意是無論別人做什么,這一策略(自我目標)總是想使自己的目標最大化,。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想采取不同于占優(yōu)策略的策略(更合作的策略),他們的目標反而能夠得到更大的滿足,。的確,,有關研究表明,在有限重復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行為是普遍存在的,。還有,不僅在無重復的博弈中,,在無重復的現(xiàn)實生活中,,合作行為也是經(jīng)常可見的,。這些普遍存在的合作行為表明:人們清楚地理解他們的目標所在,,并希望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的最大化,由于認識到了人們成功的相互依賴性,,從而關心他人的目標,。
森因此總結出這樣的結論:任何行為總會帶有一定的社會性,。關于“我們”應該做或什么應該是“我們的”策略這類問題的思考,反映了我們對自己社會身份的認同,,包括對他人目標和相互依賴性的認同,。雖然他人的目標并不可能被納入一個人自己的目標中,但對相互依賴性的一致認同,,會給出某種特定的行為準則:這一行為準則不必具有內(nèi)在的價值,,但對于促進團體中各成員的目標實現(xiàn)卻具有很大的工具價值。
博弈論的語言很容易誤導人類,,使人們認為無論一個人表面上最大化的是什么,,基于一個簡單的解釋(如一定要最大化現(xiàn)實自己的目標),都必定是他的真正的目標,。但實際上,,一個人能最大化什么,取決于他把什么當成能夠控制的適當變量,,以及在每個博弈者看來什么變化可以被視為正確的和可操作的控制行為,。所以阿馬蒂亞·森認為,“為了一般地追求個人目標而接受特定社會準則的工具價值時,,一個人的真正目標與其最大化的目標之間的區(qū)別就會模糊起來,。”是的,,如果互惠被人們認識到具有內(nèi)在價值,人們?yōu)榱烁玫貙崿F(xiàn)自己的目標,,他們就會采取合作策略,。
三十六計,合作實是上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