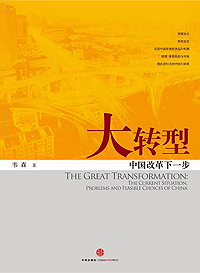 |
作者:韋森
出版:中信出版社 |
2008年,受到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奇跡的鼓舞,,兩位著名的中國經(jīng)濟(jì)問題專家勃蘭特和羅斯基著手編撰了一部“工具書”式的手冊,,這本匯集北美數(shù)十位最知名的中國經(jīng)濟(jì)問題專家和學(xué)者的論著,旨在全面分析他們眼中的“偉大的中國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F(xiàn)在看來,,2008年很可能是中國轉(zhuǎn)型道路的轉(zhuǎn)折點:北京奧運可謂中國30年改革成就的加冕禮,但隨之而來的經(jīng)濟(jì)衰退則暴露了中國轉(zhuǎn)型的另一面,,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失衡,、環(huán)境成本高企。這些也構(gòu)成了近幾年國內(nèi)外對中國認(rèn)識的雙重影像,。因此,,韋森教授的新書《大轉(zhuǎn)型:中國改革下一步》顯然也有同樣的看法: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偉大轉(zhuǎn)型仍是一種“現(xiàn)在進(jìn)行時”。
中國為何能有“偉大的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韋森教授在本書“一個漸進(jìn)成型的‘中國模式’,?”一文中認(rèn)為,毫無疑問是市場經(jīng)濟(jì)的力量讓中國經(jīng)濟(jì)有今天的繁榮,。從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上來看,,這就是“華盛頓共識”政策建議的指向——經(jīng)濟(jì)開放、私有化,、自由市場和保護(hù)私有產(chǎn)權(quán),。但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又是獨特的,甚至被總結(jié)成“中國模式”,例如倡導(dǎo)國家主導(dǎo),、集中力量辦大事,、強有力的經(jīng)濟(jì)干預(yù)能力等,在2007年肇始的金融危機及至今仍在發(fā)酵的歐債危機等事件中,,中國的國家能力成為各國政要艷羨的法寶,。
那為什么要說這個轉(zhuǎn)型處在“現(xiàn)在進(jìn)行時”?因為去年以來的現(xiàn)實告訴我們,,中國模式并非沒有成本,。在四萬億經(jīng)濟(jì)刺激政策出臺后,經(jīng)濟(jì)增長雖然快速反彈,,但隨之而來的是物價飆升,,巨額信貸投放對應(yīng)的是無法負(fù)擔(dān)的地方政府債務(wù)。作為這一過程的觀察者,,韋森教授在本書中特別強調(diào)了“無為”也是個宏觀政策選項的思想,,如果調(diào)控措施太多,且花樣翻新,,反倒會使得市場動蕩不已,。
為什么會如此?韋森教授分析說,,強勢而不受約束的政府行為,,在干預(yù)經(jīng)濟(jì)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各級政府權(quán)力尋租的獨特的社會體制形式,。中國的獨特,,也在于在市場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市場被強勢政府主導(dǎo)甚至全面統(tǒng)御,。從這一點出發(fā),,國進(jìn)民退、公務(wù)員考試熱,、宏觀經(jīng)濟(jì)調(diào)控樂此不疲等種種現(xiàn)狀也就順理成章,。如果我們把30年經(jīng)濟(jì)社會改革理解成“從基于職位的權(quán)力體制向基于財產(chǎn)的權(quán)利體制轉(zhuǎn)型”,那么中國的“大轉(zhuǎn)型”確實還走在路上,。我們也不由自主地要問,,“一個經(jīng)歷了三十多年市場化改革的中國正在走向何方?”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要推行市場化改革,?在《中國改革下一步該怎么走?》中,,韋森梳理改革開放30年歷程,,認(rèn)為有三件大事要記入歷史: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小平南巡講話與加入WTO。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小平南巡講話均是以釋放市場主體的自主性,、增加市場主體的活躍度為核心的,,標(biāo)志性事件就是《公司法》、《擔(dān)保法》等一批法律的設(shè)立,,市場深化,、經(jīng)濟(jì)增長提速。
但真正的快速增長還要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正是因為入世促進(jìn)了國內(nèi)市場經(jīng)濟(jì)的體制變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jìn),國際資本尋求利潤,,要求國民待遇,,要求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為了滿足這一條件,中國開始了密集的立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行政訴訟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一系列約束政府權(quán)力的法律相繼出臺,。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jì),先要縛住政府的權(quán)力之手,,于是有了中國入世后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的黃金十年。
隨著外向型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來自國外的壓力甚至深化到“美國政府為中國老百姓謀福利”的地步,。但是,外部的壓力讓中國形成并鞏固了市場經(jīng)濟(jì),只是外部資本需要的只是一個公平的環(huán)境,,解決不了民營企業(yè)的地位問題,,也解決不了勞動力低報酬與環(huán)境保護(hù)缺失的問題,甚至他們還很享受這種獨特的生產(chǎn)成本優(yōu)勢,。因此中國改革下一步的動力,,只能回到內(nèi)部尋找。我們已經(jīng)有了市場機制,,但還沒有與良序市場經(jīng)濟(jì)相匹配的法治與民主,,這也就是溫家寶總理所說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fù)失”,。
顯然,,政治體制并不會自動改革。2007年5月30日財政部深夜公布開征證券交易印花稅消息的行為,,讓韋森意識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實是個稅收問題,是個民主預(yù)算問題,,在本書的討論中,,他將其歸結(jié)為“限制政府的征稅權(quán)以及政府財政支出要受到民選代表的實質(zhì)性審議和制約的問題”。這一認(rèn)識,,構(gòu)成了韋森教授近幾年以來的主要工作——呼吁稅收法定和預(yù)算民主,。
要縛住政府權(quán)力之手,就要管住政府的錢袋子: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也就是征稅與預(yù)算。所以納稅人要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通過法定程序監(jiān)控和審理政府的征稅行為,,以確保其行為得當(dāng),“稅收法定”也成為近代以來憲政民主國家最主要的政治理念,。由民選代表界定政府事權(quán),,進(jìn)而決定征稅額度,完成從預(yù)算到征稅的邏輯過程,。從這一點講,,稅收法定與預(yù)算民主(預(yù)算由民選代表經(jīng)法定程序決定),為公眾了解,、監(jiān)督并決定政府行為及其績效提供了技術(shù)工具,。
盡管中國的法治現(xiàn)狀還不盡如人意,但這一改革思路并非空想,,在實際運作中已相對有效地約束了政府的行為,。這從近幾年財政部的相關(guān)法律立法的控制權(quán)爭奪上可見一斑,今年7月底,,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與韋森教授主持的復(fù)旦大學(xué)經(jīng)濟(jì)思想與經(jīng)濟(jì)史研究所聯(lián)合主辦了《預(yù)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征求意見研討會,,其核心就是堅守預(yù)算民主的底線。
社會的大轉(zhuǎn)型,,說到底還是人的觀念的改變,。通覽《大轉(zhuǎn)型》,并沒有太多理論創(chuàng)新,、觀念突破,。但在這種厘清觀念、正本清源的工作中,,韋森教授自得其樂,。他梳理知識的過程,,也是點亮他自己的過程,也正是因為這種努力,,讓韋森教授在公共輿論中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力,,感染了他人。從這一點上講,,以內(nèi)政促改革的核心在于改變國民觀念,,我們需要更多的學(xué)者努力點亮自己,中國的大轉(zhuǎn)型才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