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正文
“進入這里的醫(yī)生人數(shù)過多,,且完全不成比例,?!?920年,,巴勒斯坦醫(yī)學協(xié)會在猶太雜志上向全球的僑民醫(yī)生發(fā)表了一封情感真摯的公開信,,敦促他們不要移民到這個國家,稱該地區(qū)已有85名醫(yī)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兩倍,。
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盡管現(xiàn)在以色列的外科醫(yī)生數(shù)量已增至2萬名,,但供需矛盾依舊沒有解決,。

醫(yī)學歷史學家施瓦茨教授和已故的多倫教授在他們的研究中記錄了每所新的醫(yī)學院創(chuàng)立時醫(yī)療機構(gòu)的反對意見。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哈達薩醫(yī)學院是以色列僅有的一所醫(yī)學院,。
1964年,當特拉維夫大學準備開設(shè)醫(yī)學院時,,哈達薩醫(yī)學院試圖阻止,。幾年后,兩所學校又聯(lián)手反抗位于北部城市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學院醫(yī)學院的開張,。
當內(nèi)蓋夫本古里安大學提議在南部中心城市貝爾謝巴建立自己的醫(yī)學院時,,這三所已有學院又聯(lián)合起來強烈干預(yù)。
故事在幾年前薩法德醫(yī)學院成立時再次重演,。
7月24日,,以色列計劃建立第六所醫(yī)學院,這次是在約旦河西岸的艾里爾大學,,其他學校醫(yī)學院院長的反對意見再次浮出水面,。
盡管如此,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規(guī)劃委員會仍然批準了該計劃:第一期共70名學生即將踏入這所新的醫(yī)學院,。同時,,高教委計劃將全國醫(yī)學生入學總?cè)藬?shù)提高到每年950人。
以色列擴張醫(yī)學教育迫在眉睫:在相關(guān)機構(gòu)抱怨他們接納學生能力的同時,,許多未來的醫(yī)生已經(jīng)選擇出國接受醫(yī)學培訓(xùn),。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16年,,以色列的外國培訓(xùn)醫(yī)師比例為58%,,高于西方其他任何國家。
該國衛(wèi)生部數(shù)據(jù)顯示,,進入醫(yī)療保健系統(tǒng)的外籍醫(yī)生數(shù)量在過去十年中幾乎翻了兩番,,從2007年的238人增加到去年的895人。相較之下,,申請醫(yī)師執(zhí)照的當?shù)蒯t(yī)學院畢業(yè)生人數(shù)在此期間僅從310人增加到590人,。
也就是說,未來大多數(shù)醫(yī)生所接受的課程內(nèi)容,、教學類型和實踐經(jīng)驗的質(zhì)量均由別國掌控,。可以印證的是,,來自不同國家的醫(yī)學院畢業(yè)生中通過以色列執(zhí)照考試的人數(shù)差異很大,。
大學,、高教委、衛(wèi)生部和醫(yī)院等,,牽扯部門太多,,卻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能負全責,這讓以色列自建國前的醫(yī)療產(chǎn)業(yè)怪相一直延伸至今,。
可是,,最令人困惑的是,以色列醫(yī)學院每年錄取的大部分不是當?shù)貙W生,,而是數(shù)百名來自北美的年輕人,,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根本不會留下來執(zhí)業(yè)。
為了減少外國醫(yī)學生人數(shù),,高教委已經(jīng)一再提高外國醫(yī)學生的學雜費,。可是,,包括此舉在內(nèi)的很多措施都沒能降低醫(yī)學院留學生數(shù)量,。據(jù)統(tǒng)計,,每個外國醫(yī)學生平均給學校帶來50萬謝克爾(約合13.7萬美元)的學費收入,。
分析普遍認為,以色列需要“下猛藥”,,迅速解決醫(yī)學教育危機,,因為現(xiàn)有專科醫(yī)生的數(shù)量已經(jīng)連年供不應(yīng)求,。專家極為短缺,,病人預(yù)約等待的時間越來越長,即使是在需求不高的周邊地區(qū)也是如此,。
更糟糕的是,,這種“短缺”僅停留在對社會現(xiàn)象的總結(jié),不論是以色列醫(yī)學協(xié)會還是衛(wèi)生部,,竟然沒有任何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代表醫(yī)學專家利益的組織米莎姆發(fā)布的報告稱,預(yù)約等待時間已延長至數(shù)月,。在一些需求最高的專業(yè)領(lǐng)域,,等待時間長至兩年。
很多分析人士呼吁,,如果以色列要成功解決醫(yī)生短缺問題,,需要制定一項涉及醫(yī)學教育和醫(yī)療保健系統(tǒng)的全面計劃。這一切不妨就從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做起,。


醫(yī)療人工智能遭遇三大發(fā)展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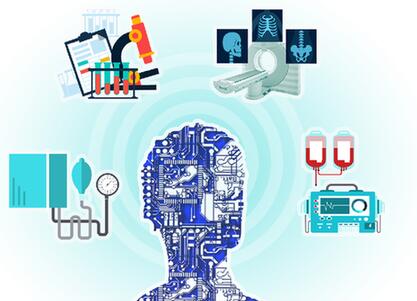
我國醫(yī)療人工智能在快速發(fā)展的過程中,面臨著三大發(fā)展困境:技術(shù)難題有待突破,,準入門檻有待監(jiān)管層加以明確,,商業(yè)模式也亟待建立。
·層層攔蓄截斷 遼河只?!鞍霔l命”
國有資產(chǎn)監(jiān)管體系建設(shè)步伐加速

針對在經(jīng)營投資中造成國有資產(chǎn)損失或其他嚴重不良后果的中央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有關(guān)人員,,形成分級分層追責和責任機制,同時對于實行重大決策終身問責,。